寒潮降临之前的一天,我们买回柏树枝,在屋顶搭了个简易得像叫化子的窝棚,但这就是薰腊肉的装置。入秋以来存下的核桃壳花生壳桂圆壳以及不少广柑壳橘柑壳,全派上了用场,隔壁的朱叔叔正在装修屋顶花园,弄了两袋刨木花,加上一堆初冬剪下来的菊花梗,足够薰五十斤腊肉了,而我却因为第一次做腊肉,怕失手做坏,只整了二十来斤肉。
在屋顶搭了个简易的棚子,薰腊肉的装置就成了。

图中的锅铲,是全铜的,是去年春节在丽江买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大都帮着父母薰过腊肉。但我家太穷,过年前最多磨点汤元面,做点汤元心子(馅)而已,加上我母亲也不是一个热爱家务的女人,她一生热衷于绣花、织毛衣,扫地抹屋,对我们一家吃的伙食总是很马虎,母亲到现在也不会做菜,却总是做一些从今天的审美看来已经过时的绣花围裙、绣花枕头之类的东西鼓倒给我们。
也许我是继承了母亲的秉性,对做饭炒菜的事,天生不感兴趣。
但薰腊肉不同,董腊肉要烧火,要烧闷烟,而人类对火的感情起源得恐怕比对抚摸猪肉的感情还要早。普罗米修斯盗火甘愿受罚;政治家玩火,跟小孩子玩火性质一样,烧了裤档、烧了房子,乃至把自己烧成残废的事,简直数不胜数,说白了,那是因为火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着绝对作用:对温暖的向往,所以在四川山里,人们把烤火说成“向火”;通过火的途径,生猛滴血的动物尸体变成了美味,而我们重庆人,是不说“薰腊肉”这种文绉绉的词的,我们说“瞅腊肉”,“瞅”在重庆话里就是“薰”的意思,那是因为,每当烟薰火燎时,眼睛都会疼痛流泪得看东西无法“看”而是“瞅”,于是眼睛瞅火,烟子“瞅”肉;而所有的矿石,都必需经过火的治炼成为钢铁,而毛老人家比我还无知,以为只要有火,石头就可以变成钢,他大手一挥,全中国的星星之火就燎了原,石头的确变成了铁,但那只是钢铁的胎胚,铁疙瘩而已。
2000年,我随电视台做的嘉陵江流域那个片子,在嘉陵江上游的陕西境内某处,当地人讲,1958年大炼钢铁时全县人民烧闷烟,把两山之间的峡谷当成了巨大柴灶,把山上的大树当成巨大柴禾,架起树棒棒烧,结果,从1958年一直烧到文革之前的1965年,那山谷里的闷烟都没有熄灭。
所以,我等虽然不爱炒菜,但一样喜欢耍火,这一点点腊肉,让我烧了两天火,只不过,毛主席耍大火,我耍小火罢了。

闷烟要烧成这样才是最高境界.


烧闷烟的过程中,罗小歪忠实地陪着我,而我全副武装,像个锅炉工,漆爷成了漆婆婆婆。

在烧闷烟的过程中,须臾不可离人。明火是不能董腊肉的,所以明火一燃,就用洋铲扑灭,烧出第一张图片那样的境界,腊肉才“腊”,否则就不是腊肉而是烤肉了。
所以每当明火轰地燃起,就要用沾了水的柏树枝去扑灭,让火成烟。结果,在整个烧闷烟的过程中我只思考一件事:古时候的烽火台,也就是这样烧闷烟的吧?
想想古时候那个天下第一粑耳朵周幽王,为了让美女褒姒开颜一笑,下令在锋火台上烧闷烟,骗诸候搬兵救驾。诸侯劳师动众,白跑一趟,当然生气,再不信他。
我想要是周幽王燃烽烟时顺便薰点腊肉犒劳白跑的诸侯,或许腊肉的香味能够让他们火气不那么大,周幽王也就垮台垮不到那么快罢。

在野外烧闷烟“瞅”腊肉,几家人轮流值班烧火,既然要照看火舌,又要注意肉肉不被野狗刁跑了。

罗小歪终于等得不耐烦,说:麻,可不可以让我先尝一口?
我用花剪剪下一块肉,洗净,烤熟,给她吃了。结果,她一出门就往瞅腊肉的地方跑,以为可以在那里搞到着儿。


腊肉瞅好了,高挂房梁,罗小歪一往情深望着肉肉说:俺肚里有肉,心里有肉,眼里也有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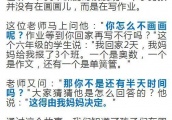



-Jk.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