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痛中解脱,是人世间最漫长的一种文明爬行。榆林产妇跳楼悲剧能否成为这种爬行的动力,哪怕只是微弱的一点?

近日,产痛成为社会公共话题。话题引发关于生育、两性、家庭、医患、制度、理性等诸多思考。
从产痛中解脱,是人世间最漫长的一种文明爬行。榆林产妇跳楼悲剧能否成为这种爬行的动力,哪怕只是微弱的一点?
■ 生育
人类历史即是一部生育史。《最美的生育史》展现了这一历程。
长久以来,生育因为难以掌控而具有和自然一样的神秘气质。自然母亲和众神之母玛格那·玛特(Magna Mater)都被想象成子宫发达的女性,子宫是繁荣和生生不息的象征。史前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制作女性陶土塑像,以此庆祝生殖。
但神秘同时也是一种莫测。起初,人们用神灵的意志来解释生育这一现象,但这催生了恐惧:假如生育是一项礼遇,是神的赐福,那么,它同时也可能成为一项重负,一种诅咒。一神论宗教宣扬胚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上帝的杰作,夏娃在伊甸园受蛇引诱偷尝禁果,是对上帝的背叛,此后上帝惩罚人类必须怀孕生子。《旧约·创世记》中写道:“我必多多加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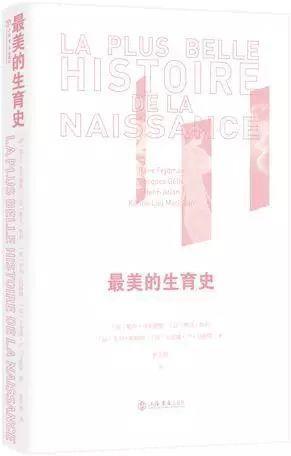
《最美的生育史》
[法]勒内·弗里德曼等 著
彭玉姣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人们设计出种种生育仪式和禁忌来消解既期盼又恐惧的痛苦挣扎。
比如,寻觅各种洗剂、护身符、药膏和偏方安胎,还有各种古怪的行为禁忌———安坐时不能交叉双腿,不能编织毛料,不能佩戴项链和手镯……中外莫不如此。
在《生育的禁忌与文化》一书的书名中,“禁忌”即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一是崇高的、神圣的;二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生育禁忌因为蕴涵了这两方面的含义,而让人们对它颇为敬畏,它不仅是人们约束生育行为的准则,而且又是作用于人们精神心理上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不但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存在,就是在现在的民间,也还有稳定的生育禁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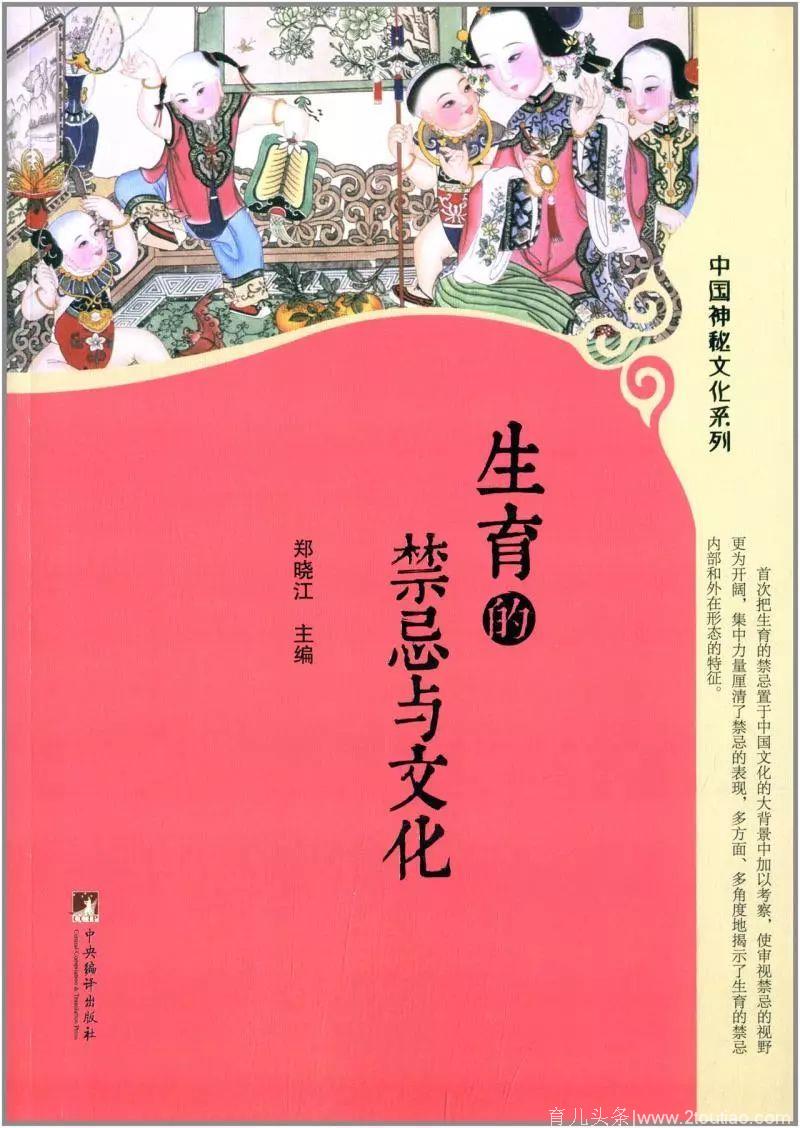
《生育的禁忌与文化》
郑晓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世纪,女性排卵的奥秘被揭晓,但直到20世纪,生育方式才发生根本性转变。1921年,玛格丽特·桑格创立美国节制生育联盟(American League for Birth Control),开女性计划生育之先河。但在当时,高出生率是经济繁荣的保障,孕妇被要求在医院分娩,以控制一些使产妇丧命的产后感染,人类在减轻分娩阵痛、早产儿护理,以及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甚至,妊娠可以不再依赖性关系。2005年,亨利·阿特朗在其畅销书《人造子宫》里提到,脱离母亲的身体,婴儿完全可以在人造子宫里生长发育。
持续进步的辅助生殖技术,也持续地引发着道德争议。过去,怀孕是偶然的结果,如今,人类有了各种各样的生育选择,却也需要面对很多伦理问题:体外胚胎只是一堆细胞组合体吗?人们是否有权随意赠送、买卖、交换和遗弃胚胎?胚胎什么时候成为人?什么时候拥有人的权力……
回顾生育演变的历史,与个人情感体验相关的生育行为总是具有非同凡响、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个体的出生又被隐匿在人口统计学空泛的数字里,直到榆林产妇的绝望一跳。
■ 两性
最初的生殖崇拜,随着社会变迁逐渐被消解,男性的心智发展受到重视,而怀孕生子的女性则被贴上“生育工具”标签,她们首先作为生育工具存在。
这种观点几乎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女性看似拥有掌控自己身体的自由,实际上,城邦处于专制政权统治下,公民最紧要的义务是为城邦生养士兵,为了养育出体格健壮的战士,女性需要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民族“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natio”,意为“生育”、“摘取”。一个国家国民数量越多,国力就越强盛,因为关系到士兵和纳税人口的增加。
在生育涉及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主张女人应受男人监护,特别是在履行怀孕生子的义务时。虽然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一些相对开化的时期,包括观念意识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升等;然而更多的是女性遭遇不公平对待,历史上对男女平等的追求从未停止。
中国是一个生产出13亿人口的大国,女性在过去的民族繁衍中采取了什么方式、遭受了怎样的苦痛、经历了哪些变化?《产事》记录了她们所经历的分娩习俗和文化,以及她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歧视,这是民族记忆中不可缺少的关于“生”的历史。而其中,中国近一百年的生育史尤其变化丰富。产事既是私人的,也成了历史在大变动时代的记载。

《产事》
刘冰、钱序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当社会将生育定性为女性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时,女性也很容易将生育视为自身价值的实现。不能生育的女人大多被遗弃、被驱逐,直到今天,女性因不能生育而遭受暴力侵犯仍是社会现实。
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剖与不剖的问题上,即使榆林产妇表达了明确的意见,却依然不能决定自己的生育方式。因为剖与不剖,是附着于生育过程中的,当女性或显性或隐性地被视为生育工具时,她是没有选择权利的。从单身女性没有生育权,生下的孩子无法上户口,到已婚妇女生孩子无法选择生产方式,莫不是这种“工具”观点的映射。
女性研究学者李小江在《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中谈到,从立法层面看,今天的女人走出了完全依附家庭和男人的生存困境,可以自食其力,在社会上享有和男人一样的合法权利,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从个人生活层面看,多重角色造成多重压力,对依旧承担着生育责任的职业女性来说,收获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自由,反倒多了困惑和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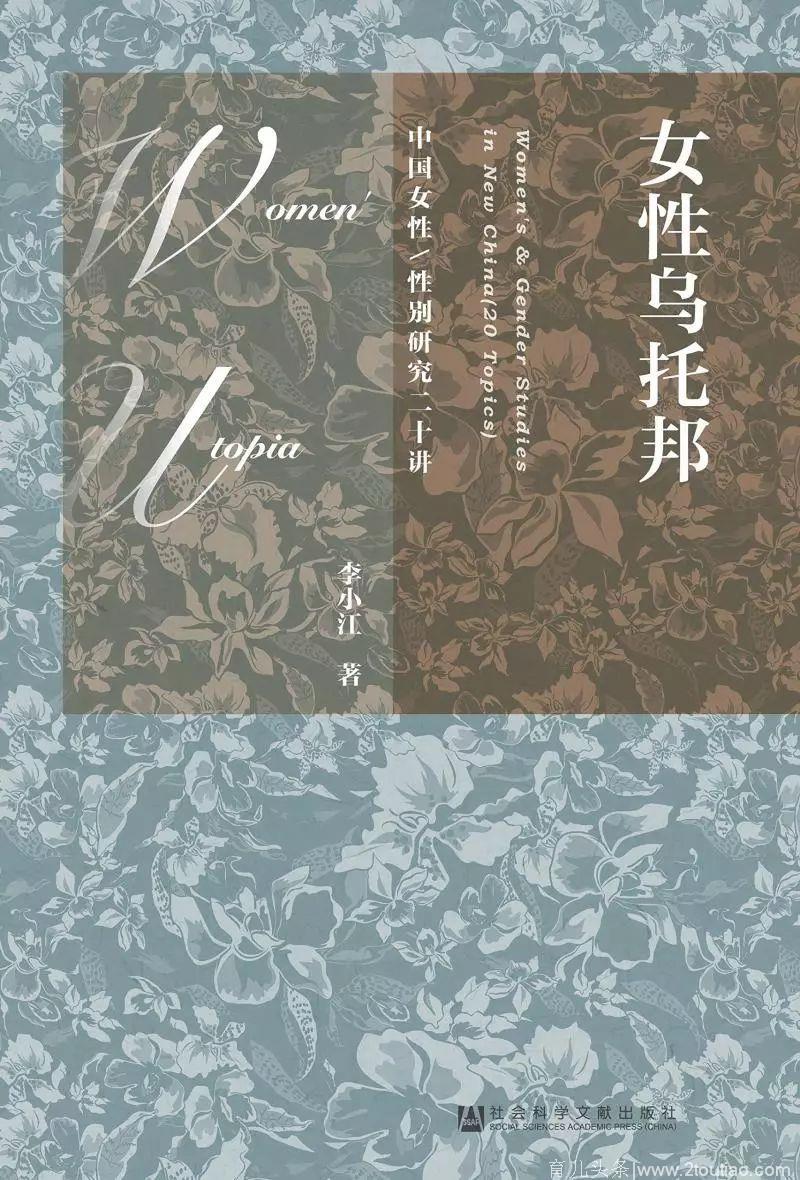
《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
李小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产痛
1843年,乔治·威尔逊,一个25岁的青年人,因大腿受伤后严重感染,不得不像当时许多病人一样,接受截肢手术。这一年恰是外科麻醉诞生的前一年。
作为医科大学的学生,威尔逊记录下了手术的感受:
“我最近怀着悲伤和惊讶交织的心情读到,有外科医生宣称,说麻醉是不必要的奢侈,难以忍受的剧痛正是极佳的精神振奋剂。我认为这些外科医生对病人真是太无情了……
我所经受到的痛苦是如此之大,无法用文字表述……那突如其来的、不寻常的剧痛如今已经淡忘,但是绝望的情绪漩流、极其神秘的恐惧和在濒临绝望之时觉得要被上帝和人类抛弃的感觉,穿透我全身,充溢着我的心,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若在接受手术之前……我能凭借乙醚或者氯仿让自己处于无感觉状态,我就可以免除所有这一切的剧痛了。”
产痛并不比截肢之痛轻微多少。“断了十二根肋骨的疼痛”、“小腹曲线型爆炸疼”,“被人用大锤抡小腹,抡了八小时”……这是“知乎”上亲历者们关于产痛的描述。而据一位医院产痛体验活动的现场观察者描述:准爸爸们在肚皮上接上可以用电流模拟宫缩刺激的分娩阵痛体验仪,两位准爸爸中的一位在4级疼痛时全身颤抖,赶紧叫停,另一位坚持到了7级,几秒钟之内,他面部抽搐,出了一身冷汗。而分娩期间,产妇可能要面对的是10级疼痛,时间长达数小时、十数小时,甚至是数十小时。
但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对产痛的医学干预一直不是主流,感动了全球无数女性的普利策获奖作品《天空的另一半》中写道:“麻醉剂被研发出来后,几十年来不让分娩妇女使用,因为妇女受苦被认为理所应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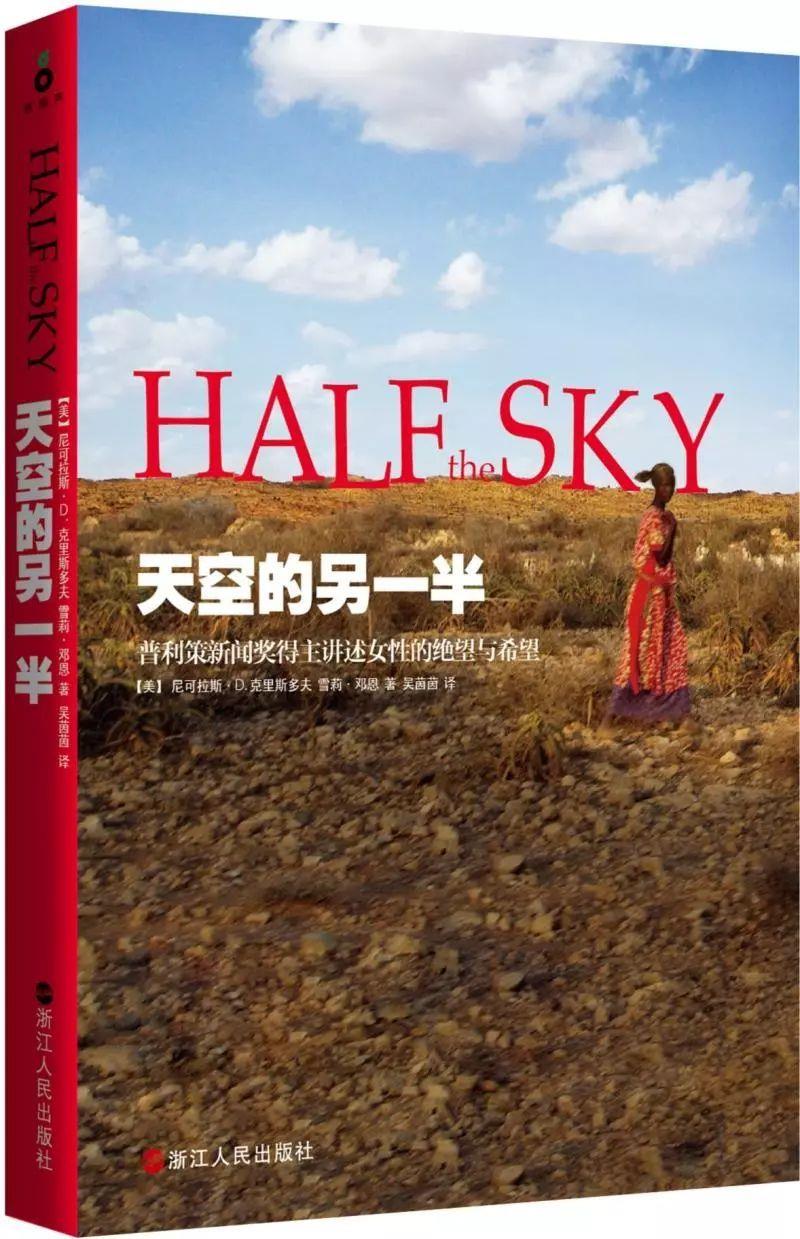
《天空的另一半》
[美]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 雪莉·邓恩 著
吴茵茵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英妇女发起了要求无痛分娩的社会运动,同时代的中国也没有落后很多:1964年,有67名中国孕妇做了无痛分娩。但之后却停滞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无痛分娩和重症监护几乎在同一时期重新起步,但到了2011年,重症监护几乎遍及每家医院,而在2004年的公开报道中,无痛分娩的发展状况是:“尽管相关技术20年前就已经成熟,但中国年均2000万名产妇中,迄今累计只有约1万名享受到了无痛分娩,比例不到1%。”而同期美国的比例是61%。今天的欧美国家的无痛分娩比例已高达80%以上,而中国目前仍未到10%。
尽管已经有了很多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无痛分娩的安全性,但为了避免所谓的对胎儿的“不良影响”,在剧烈的产痛下,大量的产妇选择剖宫产。数据显示,中国的剖宫产率为世界之最,达到46.5%,超过世界警戒线3倍多。
而实际上,硬膜外麻醉所用的浓度只有手术麻醉时浓度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到达胎儿的剂量微乎其微,其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知识在2011年度“世界麻醉研究会杰出教育成就奖”获得者、世界著名麻醉教育家胡灵群主编的《你一定要知道的无痛分娩: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中都有详尽的说明。

《你一定要知道的无痛分娩: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
胡灵群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当然,无痛分娩在中国比例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医院缺乏实行的条件。无痛分娩需要麻醉师和医生的协作才能完成,但在中国,麻醉师数量稀缺。2014年有媒体报道称,我国至少需要30-35万名麻醉师,而目前只有近10万名。即便在医疗水平发达的上海,麻醉师都非常稀缺,许多麻醉师每天工作超12小时,需要负责2到3个手术间。上海尚且如此,全国各地麻醉师的稀缺状况可想而知。
这显然是下一步医改需要关照的内容。产妇分娩是否痛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反映了一种生育文明。
■ 医闹
榆林产妇要求剖宫产,医生也说有指征,最终却没剖,是不能,还是不敢?
关于能不能,有律师指出,在知情同意权与签字制度上,“我们现阶段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还存在一些法律冲突。”
比如,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是将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或关系人并列为接受告知的对象:“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但《侵权责任法》第55条则明确患者才是接受告知的对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无论是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还是法律效力高于条例的原则,患者本人都应该是自己身体的主宰。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后,不少医疗机构明白不能再让家属签字了,但只让患者签字感觉没有“安全感”,于是有部分医疗机构想到了授权委托书———让患者授权他的某个近亲属全权处理他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知情同意,于是,产妇家属,一般是丈夫,还是以签字的方式决定着生育的方式,而方式有时决定了生死。榆林产妇的情况便是如此。
能不能的问题就此转换成敢不敢的问题。
本是专业和权威的一方,医院为何变得畏首畏尾?有在医院工作的网友写下这样一段话:“以前是允许产妇自己签字的,但结果往往是剖完了家属就开始闹,说医院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大部分的产妇也会跟着反咬医院说自己当时疼得意识模糊就签了,所以我们医院现在要求产妇和家属都签字。”
还有网友披露:“我们这里的医院去年就有一单。医生连续几天劝说家属签字剖宫产,说明了顺产的种种不可能性,但家属始终拒绝签字,最后孩子胎死腹中。家属拉横幅、打医生,哭诉‘无良医生,还我孩子’。”
家属同意本来不是必要条件,但是被紧张的医患关系复杂化了。榆林产妇的真相尚未可知,但抛开此个案,医患关系紧张是不争的现实。
据《医学不能承受之重》主编之一的青年医学专家苏佳灿介绍,仅最近五年,曝光的伤医事件就有数百起:“温岭杀医案”“哈医大血案”等一系列恶性事件,不断震颤着社会的神经;“丢肾门”“缝肛门”等谣言,荒谬如斯,却能“刷屏”……藏在污医谣言和伤医事件背后,是这样一个事实:医学正承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人们对医学的风险性、局限性、不确定性了解甚少,以致对医学有着过高的、非理性的期望;医学知识的缺乏、医疗信息的不对称,让人们对生活和健康的本义有着诸多的误解;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压力也会转移到医患纠纷中……
这些医学不能承受之重,其影响是双向的,它在使患者变得更焦虑的同时,也使从医者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宁愿躲进冰冷的仪器和程序化的操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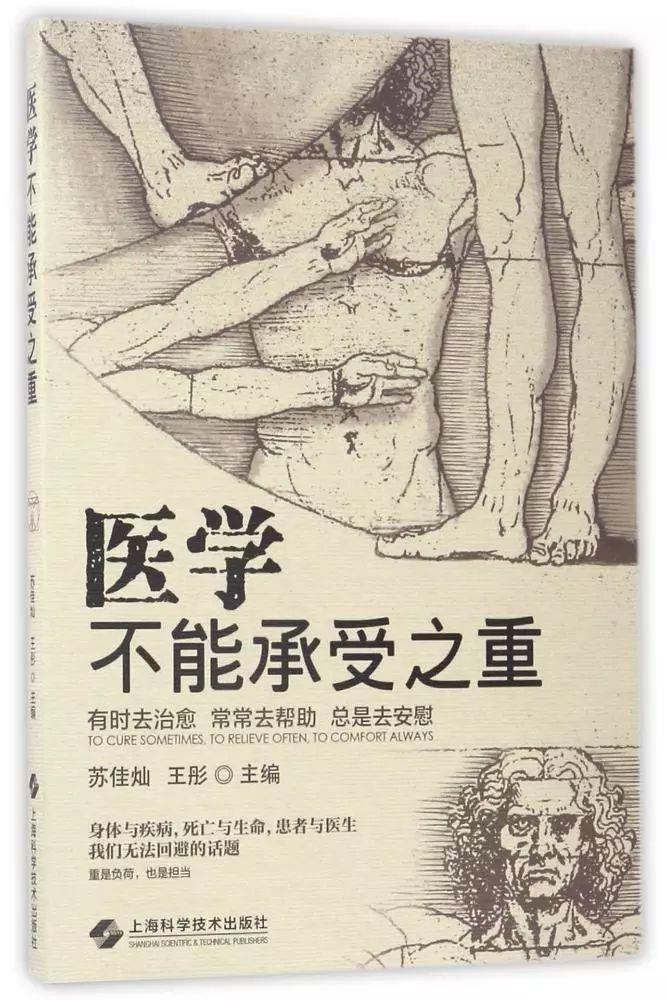
《医学不能承受之重》
苏佳灿 王彤 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医学不能保有它使命中本该有的科学精神与人性温度,受害的是我们每个人。
在最近刷屏的对马东的某档采访节目中,当采访者质疑《奇葩说》所讨论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被讨论过时,马东回答:“那我们的民智开了吗?”
确实,今天的我们,挂在嘴边的话题可能都已经不是互联网,而是人工智能了,但科学的巨大进步并未明显减少愚昧与偏执,科技扩大了人与人的连接,同时也加速了人与人的分裂和认知的分裂。
不管学历高低,很多男性思想中依然残存着男权主义,他们对女性持有物化态度和工具主义。
在全球销量2000万册的《醒来的女性》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她们在英语课上上《驯悍记》,她在圣诞节收到了《源泉》,又读了一遍。她又试着读尼采的作品,后来发现,他说女人们是骗子,说她们狡猾,试图控制男人。他说,你去见女人时,应该拿一根鞭子。那是什么意思呢?没错,她的母亲确实会使唤父亲,但母亲并不是骗子。米拉也撒过谎,但只是为了不去上学……老师说,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可当他们在米特劳家吃晚饭时,肥胖的米特劳先生会对他的妻子吼道:‘牛奶!’尽管她和他一样高,也非常胖,她还是会从桌子旁蹦起来,忙不迭地拿来一壶牛奶。有时候,他们会在夜里听到哭喊声,然后沃德太太就悄悄对米拉说,那是威利斯先生在打他老婆。沃德太太还告诉她,街对面住了一个德国屠夫,只有他和女儿两个人住,每当他晚上想出去喝酒时,就用链子把女儿锁在床上,喝完酒回来还会打她。米拉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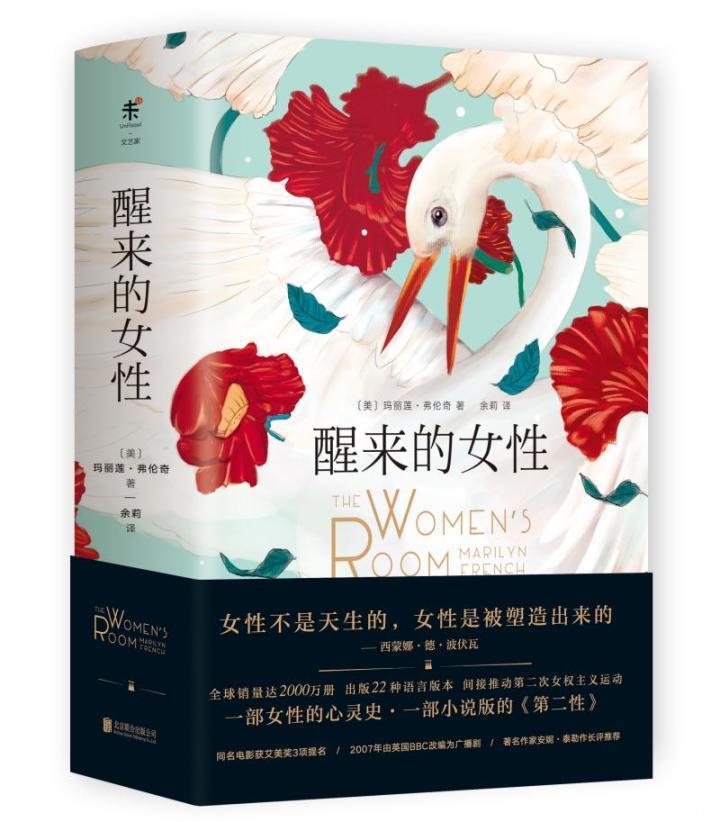
《醒来的女性》
[美]玛丽莲·弗伦奇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一部反映了整整一代美国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有媒体称:“你常常会忘了这是一本小说,书中所写的都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如何书写“最美的生育史”,在今天,依然是个社会命题,但很多人的努力,还是使它走出了最暗处,正在努力地走向美好。
(本公众号和上观新闻APP上书房栏目专稿)
这是“朝花时文”第1346期。请直接点右下角“写评论”发表对这篇文章的高见。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投稿类型:散文随笔,尤喜有思想有观点有干货不无病呻吟;当下热点文化现象、热门影视剧评论、热门舞台演出评论、热门长篇小说评论,尤喜针对热点、切中时弊、抓住创作倾向趋势者;请特别注意:不接受诗歌投稿。也许你可以在这里见到有你自己出现的一期,特优者也有可能被选入全新上线的上海观察“朝花时文”栏目或解放日报“朝花”版。来稿请务必注明地址邮编身份证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