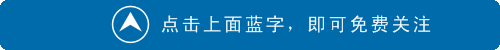
文:司葆华
在那个一日三餐清汤寡水的年月,村子里家庭主妇们把调剂生活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因陋就简创制不少家常风味小菜,给寡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滋味。

在那些的家常小菜里,腌咸豆子是家家户户的日常必备。场光地净一入冬,刚刚放下农具的妇女们就开始张罗腌豆子。拿出平日少有的慷慨,将大半筐子的黄豆洗净蒸煮,然后放到保温性能很好的草编囤子里,再将囤子搬到场院自家麦秸垛里捂闷发酵。
几乎每家麦秸垛里都在隐秘地进行着这个家常菜的前期准备。所以秘而不宣地悄然进行,除了防着那些贪食的猫狗,主要担心被时常来这里捉迷藏的孩子们毁坏,而让多日的准备前功尽弃。主妇们只要来场院里取生火的柴草,就不声不响地扒开麦秸,看看豆子发酵情况。
她们以很好的耐心和黄豆慢腾腾的化学变化较劲,注意把握着温度,掐算着时日,这个等待的过程相当熬人。待到黄豆色泽开始一点点乌青发暗,她们差不多已经成竹在胸。再等到颜色越发暗重的豆子长出点点白斑,开始散发出淡淡霉味的时候,她们知道自己腌制工作几近大功告成。前期的捂闷发酵可以说关乎腌菜的成败,成色,口感,甚至整个腌菜的风味好坏都在此一举。

接下来,她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一道工序,下菜。把早就准备好一口土坛子擦洗干净,把切成丝缕的白菜、萝卜和冬瓜装进去,一层层撒上粗盐疙瘩,有条件的就再放些作料,然后把坛子封口若干天,以便腌菜充分入味。
有发酵好的黄豆打底,腌菜成功将指日可待。但馋嘴的孩子总是亟不可待,美味的诱惑常常叫他们把母亲的告诫忘到九霄云外,从腌菜一入坛子那天起,就不知道偷偷摸摸尝过多少回。待开坛之日,看看原本平整齐崭的坛子口给扒弄的一片狼藉,当母亲的当然心知肚明,嗔怪地瞪一眼身旁一脸馋相的孩子:“老鸹等不到桑葚黑,还能少了你吃的不成?”。
开坛的腌菜仍色泽如初,白菜依旧莹白,萝卜依旧青绿,冬瓜则在晶莹里多了几分柔嫩。吃起来白菜萝卜脆生爽口,冬瓜则柔韧劲道,两种配菜的腌豆味道真是各有千秋。

坛子打开口,腌豆就开始呼呼啦啦占据家家户户的饭桌,无论是烙饼子,烧米粥,焖干饭,还是煮疙瘩,擀面叶,蒸馍馍,不管你吃什么,拿这腌豆下饭,就如一件可身的衣服,真是百搭。稀里呼噜地喝着饭,咯咯吱吱地嚼着菜,吃的畅畅快快,味蕾舒展伸张。简单至极的淡饭粗茶,吃出山珍海味的饕餮快意。腌豆在那个时代简单的口腹之乐中可以说居功至伟。
母亲做的腌豆到现在都影响着我原本一点都不挑剔的胃口。通常早饭时没有腌豆,就拿咸菜来凑,对这类寻常百姓小菜的喜爱真是深入骨髓。口味上的偏好如此根深蒂固,叫我这么些年来对自己这个老土的习惯一直不思悔改。几乎无一例外的,每每在一顿鱼肉荤腥之后,不去喝着稀粥就点咸菜什么的,总觉得委屈了自己的肠胃。
现在村里入冬时节再也没人腌咸豆子了。作为乡村曾经的标识和符号,那些蘑菇一样的草垛早已消失的不见踪影,自然,失去发酵环境的腌制也就没有了可能。

再说了,世易时移早已改变了人们的口味和习惯,现在从大超市到小商店里袋装佐餐的所谓风味小菜形形色色。购买的方便快捷取代了那种传统腌制的讲究和繁琐,这些工业生产线上的即食产品强势而霸道地占领了百姓的餐桌,格式化了人们的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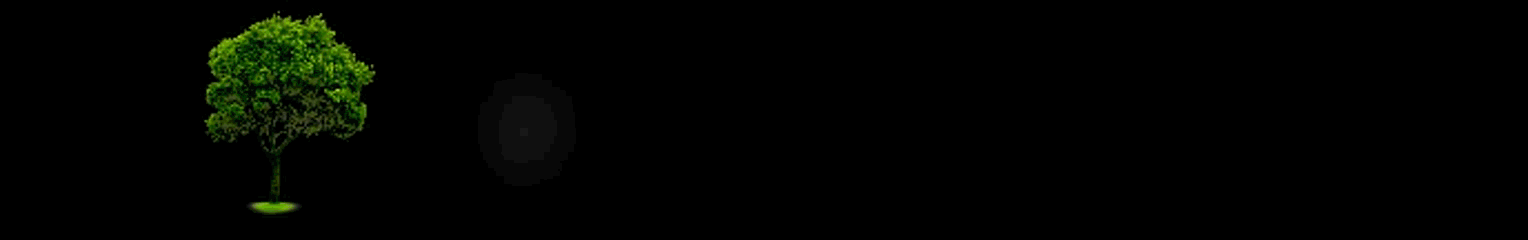
腌豆味道的醇厚绵长,只能永远存放在一代人舌尖上的记忆里了。





-J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