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问题是胎儿地位的核心问题。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段尤其早期,杀死畸形的婴儿都曾经是道德和法律所允许的,甚至是法律所要求的。但随着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发展,尤其是宗教观念的发展,胎儿的地位问题开始复杂化。在中世纪西方的道德和宗教传统中保护胎儿禁止堕胎的观念已经形成。中世纪的基督教认为,一切形式的堕胎都是违反教义的,不论它是出于什么原因。历代教皇均对堕胎持反对态度。近代新教的两个主要创始人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胎儿自受孕开始就具有完全的人性,堕胎就等于杀人。反对堕胎也在中世纪以来的法律尤其是刑法中体现出来,如1630年的英国法律规定,出现胎动(约16周)以后的堕胎为仅次于死罪的大罪。1803年的英国法律进一步规定,一切堕胎都是犯罪,胎动后堕胎则处罚更重。1861年英国法律又规定,对任何企图引起流产的行为,不管由孕妇或其他人所为,都判为重罪,这一法律一直实施到1967年。天主教是反对堕胎最高调的团体,《1983年罗马教廷家庭权利宪章》阐述了天主教对避孕、绝育和堕胎的严厉态度。伊斯兰教也明确禁止堕胎,1990年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主张“胎儿和母亲都应受到保护和特殊照顾”。冰岛在1983年有关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之后,加强了《1861年对人犯罪法案》中有关禁止堕胎的规定,堕胎仍然被作为杀人罪加以惩处。在亚洲,至今尼泊尔的被确定犯有自我流产行为的妇女还会被判处长期监禁。

但从20世纪以来,堕胎在总体上表现出自由化宽松化的趋势。在目前胎儿宪法地位的这两种模式中,采用美国模式的国家要更多一些。“从世界各国宪法保护胎儿生命权的基本趋势看,适应解决方式是保护生命权价值的基本政策。”但就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说又有差别,有的国家如1990年的比利时和保加利亚正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另一些国家如1992年的波兰和德国则向着对堕胎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的方向发展。不过即使是更加严格地控制堕胎,这种严格也是相对而言的,总体趋势上看还是宽松了。具体表现是:首先,医学原因的堕胎、犯罪原因的堕胎和伦理原因的堕胎得到较普遍的允许。其次,基因原因或优生学意义上的堕胎也得到较大程度的容忍,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如《德国基本法》就禁止基于这种原因的堕胎。再次,除此之外的堕胎行为尽管在有些国家还属于违法行为,但却被除罪化了,即免予刑罚处罚,如德国的规定。导致堕胎宽松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自由权尤其是妇女的自由权的认可和尊重。强迫性的生育对妇女而言其打击必定是毁灭性的。除了继续妊娠可能会危及孕妇的生命的情况外,“如果怀孕是因为乱伦或强奸,或者,如果胚胎具有先天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畸形,那妇女所受的创痛就愈加强烈。……一个妇女如果拼命寻找堕胎的可能而无视刑法的惩罚,她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如果她屈服于刑法,那么她的生活就可能被摧毁,同时她的自尊也会被抛弃”。在禁止堕胎的国家和地区,堕胎其实从来就不曾真正被禁止过,法律的禁止只是令这些私下里进行的非法堕胎手术的条件更加恶劣、手术更为危险,更加剧了妇女所承受的伤害。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压力和优生优育,为此而对堕胎采取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

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人”这个概念,才可以放心地主张“胎儿不是人、胚胎不是人”。首先应认识到,是否允许某种条件下的堕胎与是否承认胎儿是“人”且是宪法上的“人”,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问题。基于胎儿的生命对孕妇生命的可能威胁、基于胚胎的生理缺陷、基于人口压力即胎儿的出生可能将会威胁到其他现实人的利益、基于大部分避孕措施的堕胎实质性和意外怀孕的胎儿对孕妇自由的影响等理由,而否定胎儿是“人”且是宪法上的“人”的观点,都是值得质疑的。“从根本上说,出生权利的悖论是由人权的绝对性与现实物质条件的有限性的矛盾产生的。”这些问题都是从现实的自私的功利性出发提出来的,而且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在承认胚胎的主体资格之后解决的人权冲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难以取舍就干脆否定胚胎的主体资格从而取消这些问题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这不应该是解决胎儿地位问题的正当且最优的方法。
功利主义之外,另一种否定胎儿是“人”的主张是基于意识能力标准。如德国学者Norbert Hoerster认为:“赋予生命权保障的合理依据是权利人是一个有位格的生物,即有自我意识以及理解能力的生物。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生物才会意识到死亡、预期死亡的恐惧,国家才有必要以‘禁止杀人’的方式来保护他。而胎儿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就不应享有生命权的保障。”这种观点也是值得质疑的。如果完全无视人性尊严的思想,仅仅把人格理解为经验科学的外在智能的有意识理解能力等,“则不仅仅是胚胎、胎儿,甚至新生儿和重度精神病者、白痴等都不具有人性。不要说中止妊娠,就是杀婴在道德上也是允许的”。因此,“所有将生命起点往后延至胚胎营巢时、脑神经开始发育时、胎儿脱离子宫的存活能力、或是迟自诞生的一刻等,这种对人的定义观点不管是出于质或时间的观点,都在定义上否定了生命权及尊严保障的可能”。

从根本上说,对“人”的定义只能是生物学——物理学的定义。“承认胎儿亦应享有生命权的保障,其最坚实的根据在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些负面经验。今天基于这样的观点来定义怎样的生物有资格享有生命权,明天又可以基于另一种观点来定义享有生命权的资格,如是则生命权的保护与否就可以任由立法机关来任意操纵了。因此,只有以生物学——物理学的方式来定义生命,才能符合保障生命权的目的,使其免于受到由不同的社会、政策、种族观点出发来评价生命的危害。”
基于上述理由,敬畏生命,就应当承认胎儿是人,从人权理论的角度应当承认胎儿的人权主体地位。但由于胎儿与孕妇的关系是一种极度紧张的关系,生理上的关联性使这种关系与其他任何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区别,从而,适用于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并不能在胎儿与孕妇之间一律适用。因此,堕胎在一定条件下得被法律容忍,堕胎的条件需要法律来作严格明确的规定。例如,一般情况下孕妇有继续妊娠的义务,且有较好的环境与条件帮助孕妇来完成妊娠和生育。但当确实需要在孕妇的生活利益与胚胎的生命权之间做出选择时,常规的避孕和孕早期的堕胎应属孕妇的私生活权。而在胚胎具有了母体外存活能力及其大脑发育完善到足以感知疼痛之后,胚胎的生命权就可以压倒孕妇的生活利益,堕胎应该禁止,除非怀孕是因为乱伦或强奸所致,或者胚胎具有极为严重的先天性生理或智力障碍,或者胚胎的继续发育会威胁到孕妇的生命。堕胎实质上是以牺牲胎儿的生命来换取其他利益,只能是人类万不得已之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且是最后的选择,实不应该成为人类的轻率之举,尤其是把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的办法无疑是对生命的漠视和践踏。同时,胎儿的生命权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作为人权的主体,胎儿的尊严权却是绝对的,即使在堕胎时也应该对胎儿保持应有的尊重,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要求。

因此,在胎儿宪法地位的两种模式中,本文认为从保障人的生命与尊严角度而言德国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优。应承认胎儿为宪法上的“人”,是生命权的主体,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另外,还应扩大胎儿权利的范围,认可胎儿不仅仅享有生命权,也享有健康权和请求权等。此外,借鉴德国“不足禁止标准”的法律规范手段,在保护胎儿规制堕胎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个体的隐私权和自由权。
我国包括现行宪法在内的几部宪法都没有对胎儿的宪法地位做出明确规定,2004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但宪法仍然没有明确“人”是否也包括胎儿。尽管在其他一些部门法中规定了一些有利于胎儿保障的条款,如继承法中为胎儿保留继承份额制度、刑法和刑诉法及劳动法中对孕妇的特殊保护。但继承法的规定又以胎儿“出生时非死产”为条件,可见保护的并非胎儿的利益,而是出生后的人的利益。这与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相一致。相反,如果是承认胎儿为人的话,那就不应该是为胎儿保留遗产份额而是应直接由胎儿参与继承遗产。我国的刑事法律中对孕妇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但却并非基于对胎儿主体资格的承认,因为孕妇可以选择堕胎,而堕胎后的孕妇也不能适用死刑。劳动法中对孕妇的保护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另外,在法律层面的规范体系中找不到一般意义上的禁止堕胎的条款(法律只禁止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见下文),孕妇几乎可以毫无法律障碍地堕胎。故上述这些部门法条款还不够充分推断出胎儿是宪法上的“人”、是生命权的主体,胎儿至多只能算是潜在的人、独立的生命有机体。另外,我国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宪法》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际上对以计划生育为目的而采取的堕胎手段持容忍和放任的态度,避孕措施的宣传和鼓励应视为对妇女生命健康的保护。在强大的人口压力下,为推行计划生育而实行的包括准生证制度在内的各种严厉的生育制度并不阻止妇女施行妊娠晚期的堕胎。另外,近几年来为纠正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法律和一些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又对计划内妊娠中晚期的堕胎设置了种种障碍,如堕胎许可证明制度、堕胎查验证明登记报告制度及处罚制度等。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实践来看,胎儿在我国宪法上应该是只具有客体的地位。宪法保障的是出生率、人口性别比、已出生人口的生命健康,而不是孕妇的生育自主权,更不是胎儿的生命和尊严。

由上所述,我国对于计划生育外妊娠不论胎儿的生长月份而一律允许甚至支持堕胎的做法,不仅瓦解了德国模式中尊胎儿为宪法生命权主体的价值基础,也瓦解了美国模式中禁止妊娠晚期堕胎的价值基础;却从调整性别比出发,对计划生育内妊娠中晚期禁止堕胎,从而又一次瓦解了生育自主权。生命的价值与自由的价值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因此本书认为,我国宪法需要斟酌其对待胎儿的方式,并对堕胎规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前述两种较成熟的胎儿宪法地位的模式中,比较而言,德国模式更符合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不过德国模式也对国家、政府、社会及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国家而言这种模式全面实行会相当艰难。而在承认胎儿宪法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从德国模式上退一步,采纳美国模式对妊娠晚期的堕胎予以一般性禁止的做法,则更显得切合实际,尽管这种选择同样存在着诸多困惑与难题,但毕竟向着尊重生命、保障人权前进了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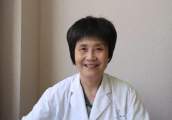




-z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