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求子旅馆里,42岁的失独母亲徐丹(化名)听见楼上的孩子下来玩,赶紧拿着刚买的橘子给孩子剥开。张赫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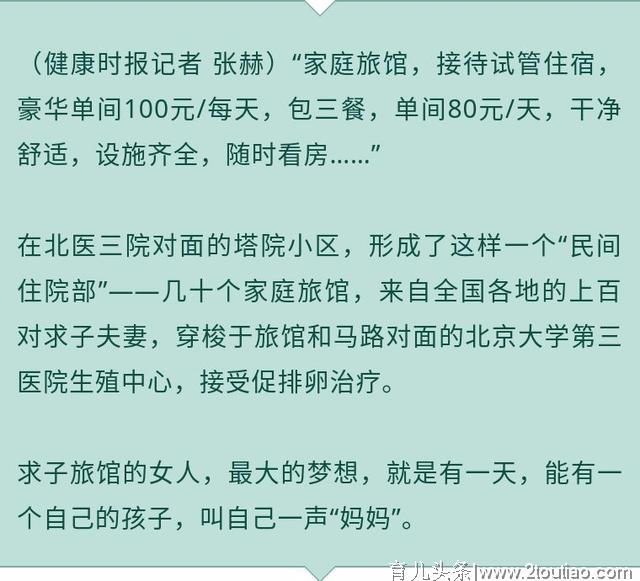

北医三院对面塔院小区一家家庭旅馆里70元/天的四人间,一个人配备一个柜子。张赫摄
没什么比要孩子更重要
一张双人床,一个简易木桌,一个立地衣柜,还有一个只有四个频道的老式小电视,就是这间150元/天的“豪华”单间的全部配套。在塔院小区的所有家庭旅馆里,这种规格的房间属于高配。
“没有啥比要孩子重要,我们来了几个月了,还没回过老家。我婆婆说了,啥时候要上孩子,啥时候就是新年。”29岁的王月(化名)和31岁的老公潘龙(化名),这对来自甘肃省陇南市农村的小夫妻,在2019年度过了离家在外的第一个新年。
2018年11月17日,在老家因先天性输卵管疾病被多次诊断不孕的王月在老公的陪伴下来到了北京,直奔北医三院,他们知道,试管婴儿可以让他们怀上孩子。
“我俩是在兰州打工时候认识的,结婚6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两年前家里长辈着急催着我们去医院检查,这一查才知道我输卵管有问题。”王月盖着被子坐在床中间,“他对我好,一直陪着我,我才没怕过。”
29岁,是女人生育的最佳年龄,但王月夫妇的问题并非个例。2018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758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出生率由12.95‰下降至12.43‰。与此同时,国内每年约有20万试管婴儿出生,不孕不育是主要原因之一。
“身体状况一切都正常的话,两个月就能怀上,过了经期就可以‘进周’,打针促排卵,卵泡成熟取出来,然后在男方体内取精,几天后受精卵放入体内,14天后抽血,就知道有没有怀孕了,没有怀孕就继续做。”
整个试管婴儿的过程,被王月说的云淡风轻,在旁边看电视的潘龙听到这,插话说,“促排卵针有进口的和国产的,我俩商量后,听了医生的建议,选了国产的针,事实证明效果也挺好,因为就在今天(正月初五),王月刚刚抽完第14天要检测的血值——我们成功了。”
“还好媳妇幸运,之前一直害怕会很疼,但其实就是在屁股上扎排卵针,和平时打针没有太大区别。”潘龙一边嘿嘿笑一边告诉记者,21天时再抽血,如果还是正常,孩子可能就稳定了,媳妇不遭罪,他就满足了。
在电视下的简易木桌上,放着两碗吃完的馄饨和一小碟牛肉,潘龙说,来北京的几个月,媳妇想吃啥他都马上给买,生孩子不容易,他知道王月的辛苦。
“这是我俩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是一想起来可能明年回家都有宝宝了,就开心的不得了。”王月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双手,一旁的潘龙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满眼宠溺地回头看着王月说,名字我都起好了,接下来就看你了。说完,小两口哈哈的笑了起来。
这间只有8平米的小屋里,空气都是温馨和充满希望的。但并不是所有求子旅馆的顾客都像王月这么幸运。

湖南湘雅医院对面小区里的“试管住宿”。湘雅医院 张越琦摄
二胎是失独父母的出路
不到9平米的隔断间里,只有一个床头柜,上面除了挂着一个插排,还有一张三口人的合影,只是如今,在中间被爸爸妈妈抱着的女孩,已经不在了。这张照片,是从黑龙江老家千里迢迢带过来的。“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花花(化名)还在呢,她就在那写作业,吵着说想吃各种好吃的……”41岁的徐丹(化名)是来自黑龙江的失独母亲,说起如今的求子之路,她最先提起的,是6年前去世的女儿花花。
失独,是如今试管求子中最大的占比原因之一。
2016年1月1日,“二孩”政策在我国全面放开。就在人们感叹80后、90后成为“史上唯一一代独生子女”时,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却因种种原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近年来,这一数字仍在持续攀升。
徐丹是这百万悲剧中的一个,6年前,女儿因为车祸去世。在那以后的4年里,徐丹完全不能工作。家中女儿房间的桌上,永远摆放着两瓶冰奶茶,她说,花花生前特别喜欢喝,但自己经常不给花花买,现在恨不得每天换一杯摆在那;她还经常买新衣服,在女儿的衣柜里,从夏天的裙子到冬天的羽绒服,一应俱全,有的还挂着标签。
“和她说说一天的生活,让她知道妈妈过得很好。”徐丹说,最开始的几年,每天都要轻轻地抚摸这些衣服,轻声的和花花说话。提起此次来北医三院,徐丹看向了床头摆着的女儿的照片说,因为两年前自己因病住院后,突然想起花花临走之前还有个遗愿,她希望爸爸妈妈到老了有人照顾。说到这,徐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39岁时,女儿都走了4年,和丈夫重新面对事实,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力不从心了。”在小心翼翼询问丈夫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让徐丹坚定尝试试管婴儿:“咱得让花花放心,要是老了没有人照顾,孩子肯定惦记啊。我不想让她心疼。”每每说到这,徐丹和老公都会抱着哭。
10月12日,徐丹在丈夫陪同下来到北医三院,最开始夫妻俩住在了一家家庭公寓,独立卫浴,可以做饭,一天房租230元。
“第一次的促排过程特别不顺,我身体对药物的吸收很差,所以促排的时候胚胎长得慢,大小一点也不均匀,医生也很无奈,后来没办法只能重新调整促排方案,调整方案后我取卵9个,最终配成4枚胚胎,但胚胎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徐丹说,为了节省支出,夫妻俩退掉了独居公寓,换到另一家便宜的家庭旅馆。
“虽然现在屋子很小,但是看到同屋很多年轻的小夫妻都成功怀孕回家养胎了,我就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徐丹说,这是爱花花的另一种方式,也是给自己的救赎。
女儿去世后,徐丹认识了很多失独父母,他们都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留住”自己的孩子。成都的“天堂”家里,永远保存着一本2011年的台历,那是儿子生前用过的最后一本台历,上面的每一页都写满了作业条目;西宁的“思念”将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个房间,还整日躺在孩子的床上,她说,“闻着孩子留下的气味,心里好受点儿”。
徐丹是幸运的,因为还能在阴暗中找到出路,重新踏上“求子”之路,这样的决定本身就是一种解脱。
据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调查显示,60%以上失独父母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处于抑郁状态的、饮食及睡眠不好的均超过60%;有精神分裂症状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偏执的、敌对的,均超过40%;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感到自卑的高达70%。
很多失独父母因为年龄过大,没有机会再要二胎,晚年凄凉。而在试管婴儿的大军中,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带着父母对逝去哥哥姐姐爱的寄托,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不是求子,求的也是余生活下去的勇气。为了让花花安心,我也要坚持。”徐丹说着,又望向花花的照片,低声念叨着:我都很久没有被叫妈妈了。
没有孩子,家就没了
“我记得去做试管的第一天,和老公在车上说笑着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当时想的是一次就可以成功,我俩的关系也能缓和一下。”42岁的孙明艳说,事实是,他们远没那么幸运。
“我和老公都是二婚,他有个孩子但12岁去世了,我30岁那年结过婚,但因为之前做过四次流产,第二次结婚以后怎么都怀不上,为了更好的维护这个家,必须要有一个孩子。”孙明艳和牛震都是河南人,牛震是驾校的司机,孙明艳是幼儿园老师。
“最开始,牛震一直说,只要两个人感情好,有没有孩子不重要,毕竟年龄大了。”孙明艳说,到了后来,她发现牛震越来越羡慕有孩子的人家,总有意无意埋怨,直到有一次,牛震半夜喝酒回家,骂她是“下不了崽的猪”,孙明艳才下定决心做试管。
“其他顾客好像都是两个人,只有我是自己在这做。”孙明艳指着隔壁的几家夫妻,苦笑说牛震只有“被需要”的时候才来,好像“求子”不得,只是孙明艳一个人的错。
“第一次取卵结束后,我俩都还挺开心的,本想回家等结果,可还没出医院门就被护士打电话叫了回去,说我的卵子异常。”孙明艳告诉记者,再次坐到医生办公室,医生说所取的6颗卵,其中5颗是GV期,1颗是M1期,也就是说,都是生卵,做试管婴儿不能用,被告知回家休息3个月再来取一次试试。
“噩梦连连,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卵子都不合格。后来4枚胚胎我移植了两次,第一次验孕棒验孕失败,第二次查血的时候血值非常低,并且第三天去复查的时候,血值并没有翻起来,就这样两次胚胎移植都失败了,促排加上移植,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孙明艳站在合租屋窗前,一边说,一边搓着手机,怔怔的看着外面北医三院的红色大字。对于已经40岁的女人来说,大半年,是一个让人发怵的数字。
孙明艳的“卵子不合格”,其实是很多做试管人群面临的大问题。卵子合格,是试管婴儿的第一步,除了对卵子和精子的质量要求高,整个胚胎培育和胚胎在体内的发展都很艰难。
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要先通过促排卵治疗、从卵巢内取出卵子(打一针排卵针,吸出卵子),如果像孙明艳一样,卵子不成熟,是不能进行下一步骤的,然后从男方取出精子,精卵在实验室结合,2天到5天后进行移植;培养过程中经陆续淘汰,医生最终从多个胚胎中挑出一个或几个植入女子的子宫,其余的胚胎被放进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罐中保存。
移植后14天,是所有人夜夜祈祷的日子。因为如果女子没能怀孕,就取出冷冻胚胎再次进行移植,如果成功怀孕,其余的胚胎将在液氮罐中等待被“唤醒”的机会,而这些胚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命。
孩子,也是孙明艳保住这个家最后的筹码。

在北医三院对面的胡同里,各种宾馆旅馆灯光闪烁,大多数价格都在100~300元之间。张赫摄
人生愿望就是当个妈妈
从一家旅馆到现在的5家,求子旅馆老板大宋(化名)送走了无数个或失望或欣喜的顾客,在他的眼里,试管婴儿,是一个艰难又幸福的字眼儿。
走路时,手里的钥匙串叮当作响,这些钥匙对应的是5套家庭旅店的大门钥匙。在大宋带着记者来到位于塔院附近的一家求子旅馆时,也念叨着这些年身边看到过的病例。
“前年有个36岁的山西女人在乡下的钢铁厂上班,输卵管堵塞,怀疑与工厂的黑烟有关;2号楼现在住着一个快40岁的女人,年轻时候长年昼夜颠倒,现在好不容易移植完,胚胎在子宫里裂了缝;前年有个黑龙江的年轻姑娘,自己没有问题,但是老公弱精,这才是最痛苦的;有的最长断断续续住了两年……”
大宋滔滔不绝。后来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是一个试管婴儿的爸爸。1995年,大宋和妻子结婚,一直到2005年,孩子还是没来。在东北老家,跟媳妇出门买件衣服,一路能遇到五六个熟人。对方一寒暄就问,咋还不要小孩呢?
“我俩身体其实都没问题,后来取卵,我媳妇一次能取10个,都很健康。我的精子活跃度也不赖,看不出任何毛病。可两个人的精子卵子放在一起,胚胎就是活不下去。”
2006年,大宋夫妇在哈尔滨和广州反复求医无果,来到了北医三院,开始做试管婴儿。第一次移植,等到第14天,验孕棒还是只有淡淡的一道杠——胚胎无法着床,一万多块的手术费,一个多月就打了水漂。第二年,夫妻俩在塔院小区租了一间两室一厅,一间自己住,一间租给同样来做试管婴儿的患者。
“全力要孩子,啥时候没有卵了再说。”就在夫妻俩决定再试最后一次时,奇迹出现了。今年,大宋的儿子,已经10岁了。
也是在那以后,大宋看到了不孕不育人群的庞大和无奈,在这十年里,夫妻俩先后租下塔院5套居民楼,装修后分为各种单间和床位出租,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子患者加油鼓劲。
无论是大宋还是徐月,都是如今中国家庭最真实的映射。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不孕不育者约5000万。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不孕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就像正月初五的北医三院外,小旅馆招牌灯光闪烁。对面的塔院小区每一家都亮着自己的灯火,从这些窗户望向窗外的,可能是年轻的姑娘,可能是失去孩子痛不欲生的父母,也可能是为了拯救一个家的支撑,相同的是,她们都在等,等着有一天,受精卵成功变成生命,等着孩子的啼哭声触手可及,等着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另一个小生命里,等着那一句,期盼已久或久违的“妈妈”。
正月初五,在黑龙江老家是吃面条的日子,她特意给自己下了一碗挂面。“人生愿望很简单,我就是想当个妈妈,没别的。”孙明艳一边说,一边笑了。
无数个夜晚,无数个期待着的目光,把北医三院的灯,照得更亮了。
编辑:步雯






